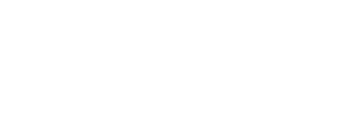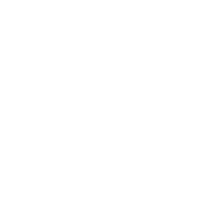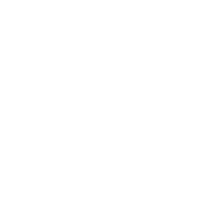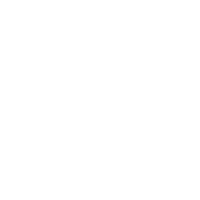贺兰山往事之总后“五七”干校有个宣传队(中)
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有一个军马场,场址坐落在沙城子,距张贤亮打造的赫赫有名的西部影视城不远。20世纪40年代初,宁夏军阀马鸿逵将“宁夏畜牧总场”改名为“十一军军马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接管该场后,将其改名为西北军区军马场,后改称“贺兰山军牧场”。1961年10月,交总后勤部军马部,改名“贺兰山军马场”。1968年10月,在此场建立“总后‘五七’干部劳动学校”,将贺兰山军马场划归干校领导。干校宣传队应运而生。

上集讲得是1969年春,总后五七干校宣传队成立至1970年冬这一年多的故事。1970年秋,宣传队奉命赴京汇报演出。随着北京演出任务的结束,宣传队短暂解散了一段时间。不久就临近1970年年底了。新年、春节都是很重要的节日,为丰富干校和马场职工的文化生活,宣传队再次集中。我就是这一个时候被招入宣传队的。
1970年12月,我加入总后五七干校宣传队,之后,宣传队共集中了4次,我都参加了。我是怎么被选入宣传队的呢?说起来这件事还挺有点意思。
那是在我当兵后的第三天,我们正在校部五七广场上练习行军礼,连部通信员跑来说指导员叫我到连部去一下。到了连部,看见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儿已经先到了,呲着一对小虎牙,非常友好地对我笑着。
指导员姓李,是位女同志。她说,你们被选到了干校宣传队,你们今天下午就到宣传队报到。从指导员口中我知道了那个女孩儿的名字:荣力军。小荣和我当时没经任何商量,但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坚决不去宣传队,要求继续留在新兵连保卫祖国。李指导员拿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我们进行教育。那时刚入伍,“一切行动听指挥”这句话在我们心中泰山压顶般神圣,不容违抗。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命令进了总后五七干校宣传队。其实我俩当时不想参加干校宣传队另有原因。就在前一天晚上,新兵连也刚刚成立了宣传队,把我和小荣也纳入其中了,结果节目还没开始排练我俩就“投靠”校宣传队了,这不是当叛徒了吗?

哪个是小荣,哪个是我一目了然吧?看她秀气的脸庞,可爱的小虎牙,是不是想到了山口百惠?
宣传队每天早晨“天天读”之后,要进行“天天练”。搞声乐、戏曲的要练嗓子,乐队的要练乐器,搞舞蹈的要练舞蹈基本功。进宣传队的第二天领导就让我们去参加“天天练”了,跟着老队员一起练习舞蹈基本功。宣传队的排练场兼练功房是校部的一个大库房改装的,南北两面墙上装着把杆儿,很宽敞。到了那里,老队员们纷纷脱下厚重的大棉衣、大棉裤开始活动。他们让我和小荣也赶紧换衣服跟着一起练。
当时我俩还一心想着要回新兵连呢,再说我们也没衣服换,就站在那里按兵不动,消极抵抗。不仅消极抵抗,还小声议论人家,反正说的都不是什么赞美之词。其实我俩无非就是想表明我们和校宣传队不是一伙的。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幼稚了!
那时宣传队的舞蹈基本功训练以芭蕾为主,超有分量的盘式录音机里播放着伴奏音乐。我还记得练五位转的伴奏是一段钢琴曲,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插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改编的。最后的跳跃组合练习音乐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实话说,我没想到宣传队的训练这么正规,这么严格,大家练得这么认真刻苦。我本来以为也就是一般地唱唱歌跳跳舞呢。寒冬腊月,他们每个人都练得满身大汗。
有两位队员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个男生,十七八岁的模样,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高颜值大长腿小鲜肉,当时我就看傻眼了,没想到生活中还能见到长得跟电影明星一样的人!这要是在今天,与林志颖、鹿晗PK也绰绰有余。关键是人家除了形象出众,身高也比林志颖、鹿晗有太多优势了。他就是在芭蕾舞《白毛女》中饰演大春的朱彦南。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规范,平转非常稳,空转也能转好几圈呢。


另一位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圆脸盘长着一双可爱的弯弯眼的女孩。我知道她就是演喜儿的那位,叫严琳。我曾经看过他们演的《白毛女》选场,她纯真靓丽的形象和优美的舞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卸了妆的她和舞台上很不一样,看起来很恬静,但基本功特扎实,控腿特别棒。这么多人里面,我觉得她练得尤为刻苦,每个动作都一丝不苟,汗水顺着她脸颊两边的头发直往下淌。

不过,由于我和小荣的思想不端正,看问题的立场不对,对他们这样认真还挺不以为然的,特别是看到有的队员,大概是因为没有练功服或运动服吧,只能穿着秋衣秋裤练,我俩还有些接受不了,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宣传队的老队员对我俩非常热情友好,无论上哪儿、干什么都叫着我们。我们加入宣传队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很多成熟的保留节目了。因为有的老队员离开了干校,我俩当时的任务就是在一些舞蹈节目中补缺。
我们学的第一个舞蹈是根据歌曲《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编排的,我们把它简称为“马舞”。它反映的是军马场的牧工身在草原心向北京、为保国防养军马的情怀。所有从贺兰山总后五七劳动干部学校出来的人都对这首歌有着特殊的感情。宣传队的队员们也都很喜欢这个舞蹈,在当时这个舞蹈绝对属于艺术水准较高的一个节目。
舞蹈开始部分有一段独唱:“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草原北京万里远,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伴随这段独唱有一段抒情表演,和我进行动作交流的是刘岩松。岩松也是一位表演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在《白毛女》中她饰演后半场的“白毛女”。我记得在干校高低不平的土台子上她能全脚尖连着做很多个“高提腿旋转加鹤立式”,现在想想,那是多么不容易,多么危险啊!
而负责教我们这个舞蹈的是老队员张维善。他是在《白毛女》里演穆仁智的,曾被专业老师评价为“超样板”——比样板戏里的穆仁智演得还像穆仁智。他特别认真负责,不厌其烦,一点一点地给我们纠正动作讲要领。小荣和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慢慢地我俩也不好意思硬扛着了,态度有了初步的改变,排练节目也开始认真起来。本来嘛,又不是什么大腕儿,还这么犟!后来,宣传队又从新兵连调来了几位队员,这大大地抵消了我俩的“负疚感”,逐渐地我们开始认同自己也是干校宣传队的一员了。

这就是《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的简谱。这首歌旋律优美奔放,干校的人差不多都会唱。
不过不知怎的,我总有个奇怪的感觉。排练间隙,一些老队员经常提议让我给他们唱首歌或者唱段戏什么的。我是天生的哑嗓子,这谁都能听得出来,而且由于贺兰山海拔高,气候特别干燥,我的嗓子整天都是干干的,处于半失声状态,他们干嘛那么想听我唱歌却不让其他的新队员唱啊?后来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原委。据说校部宣传组的一位干事曾向宣传队推荐过我,说我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行,演过白毛女,还演过阿庆嫂。我不知道那位干事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我绝对没演白毛女、阿庆嫂,更不是那块材料啊。唉!宣传队的领导和同志们见到我“本尊”之后该多受打击,多么失望啊!
1970年12月至1972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宣传队共集中了4次,演出场次超过100场,所有节目都逐步完成了由新队员补缺,复排了芭蕾舞《白毛女》第一场,对《红军帽》等保留节目进行了全面改编,大大提高了原创作品的质量,编创了以舞蹈《红色女牧工》、配乐诗表演《抗洪凯歌》为代表的一批新节目,进一步精简了队伍,逐步培养队员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也发生了许多特别令人难忘的事情。
1970年底,由于不少老队员陆续离开干校回到原单位或者调任其他工作,需要有人接替他们扮演的角色或者顶替他们在一些节目中的位置。所以我加入宣传队之后不久,又有一些新队员先后从新兵连、勤务连、汽车队、大修厂、干校第八中学等单位抽调到宣传队。队员张玉鹏就是第七次集中时加入宣传队的。他心细,完整记录了宣传队第七至第九次集中的所有演出内容、地点和场次,共82场,平均每次集中演出27.3场。第六次集中没有留下确切记录,参考第七、八、九次这三次集中演出场次的平均数保守估计,第六次集中最起码也演了20场以上。我上面说的“宣传队共集中了4次,演出场次超过100场”,实际上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

这位就是为宣传队留下珍贵历史资料的张玉鹏。他的笔记对我撰写回忆片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我回忆起了很多都已经忘记的事情。他是乐队的小提琴手和二胡演奏员,也是一位文体全能——干校乒乓球队的队员,曾代表干校到西安等地打比赛。那时他不爱说话,练琴特别刻苦,《白毛女》中“窗花舞”的那段音乐他能拉上一整天。

在我印象中,宣传队第六次和第七次集中都排练了两台节目,一台是京剧《红灯记》全场,一台是不同类型的小节目。
京剧《红灯记》是宣传队的保留节目。我在《贺兰往事之干校有个宣传队》(上)集中已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我加入校宣传队后,《红灯记》中除了扮演“祖孙三代”和鸠山(卞华清扮演)、磨刀师傅(程庭国扮演)、日本宪兵伍长(王顺德扮演)等演员没换,其他有台词的角色都逐步由新队员接替了。王连举本来由张乃栋饰演,后来由黄宝和吕森林饰演,田大婶由陈毓芬饰演,慧莲由刘岩松饰演,卖香烟的小女孩由张秀惠饰演。他们的表演也都毫不含糊,有板有眼,可圈可点。《红灯记》中有很多没有什么台词的群众演员,如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鬼子兵、不同身份的群众甲乙丙丁等。由于宣传队人数有限,我们常常一人扮演两个、甚至三个角色,需要的时候乐队和幕后人员也要上场。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服装师李老师在《红灯记》里就扮演了一位喝粥群众的角色。

这位就是扮演田大婶的陈毓芬。她真是天生的一副好嗓子,除了参加歌舞节目的演出外,还在《红灯记》中饰演田大婶,直到现在我们不少人还都叫她“大婶儿”。陈毓芬性格开朗率真,整天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在宣传队属于经常犯点儿小错误的那种,比如集合时迟个到,上台忘个词什么的,所以也经常挨个训。
《红灯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有一段戏:田大婶到李奶奶家找慧莲回家看孩子,见李奶奶给了慧莲一碗面,十分过意不去地说:“可你们家也不富裕呀”。可有一次演出的时候,陈毓芬不知怎么想的,竟把这句台词说成了“可我们家也不富裕呀”。演李奶奶的丛利见陈毓芬说错词了,赶紧接上话说:“咳!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这时田大婶应该说“我们回去了”。可陈毓芬不知为什么,又说了一遍“可我们家也不富裕呀”,这下可真把丛利急坏了的,赶紧又说了一遍 “咳!咱们两家不分你我,就不要说这些了”,语气上还特意强调了“就不要说这些了”,说着还在陈毓芬胳膊上用力捅了一下。陈毓芬这才回过味来,把戏接了下去。

这位就是扮演买香烟的小女孩的张秀慧。她化上妆,活脱脱就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她古灵精怪,学东西特别快,在宣传队主要参加舞蹈和戏剧表演。
我在《红灯记》里也演两个角色,一个是第三场“粥棚脱险”中的卖粥大嫂,另一个是最后一场戏中的北山女游击队员之一。卖粥大嫂只有三句台词:“李师傅您喝碗粥啊?”“咳!凑合着吧。”“没法子!” 那时我还不到18岁,尽管每次演出我都十分努力地压低嗓门装深沉,可只要我一张嘴,台下的观众还是要哄笑,真是“没法子”!女游击队员跳的那段大刀舞只有50秒,基本是上台走个圆场做个亮相动作就结束了。
其实不上场的时候我们也没闲着,每个队员都有任务。有的负责灯光,有的负责扩音设备,有的负责撤换布景,有的负责拉大幕。那时我们经常露天演出,为了防止舞台布景被风吹倒,需要始终有人在后面拽着布景,或者想办法用脚踩着布景框的下沿以起到固定的作用。我、荣力军、陈毓芬、张秀慧都是固定布景的中流砥柱。时间久了,台前所有演员的台词我们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几个人能从幕前曲到全剧终把整个大戏串下来。
有时候呆着没事儿,我们几个就小声聊天儿。有一次我们几个聊得太投入了,忘了时间,突然听见乐队奏起了《大刀进行曲》,我和小荣大喊一声,“坏了!”赶紧往上场门跑,并伺机混到了台上。尽管这样,也只赶上了最后的那个“嘣噔仓”亮相动作。那天把我俩吓得够呛,以为要挨训了呢,因为每场演出后都要开总结会,队领导会对当天的演出情况进行点评。没想到我俩运气真是好,领导居然没发现,我俩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除了在《红灯记》中扮演两个角色并经常参加固定布景的工作外,我还有一个重要任务:《红灯记》主要角色的服装助理。我们演出《红灯记》时,一般演员的服装都是自己保管。但主要演员服装多,而且演出时衣服不能有皱褶,需要有专人收藏保管。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主要演员的服装、服饰有一个专门的大箱子。我要记住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场戏要穿的服装以及服饰,如李玉和的“胖袄”(穿在里面的短款薄棉服,主要是为了显得身材魁梧)、毛线围脖儿,李奶奶的围裙等。演出结束后我要把所有的服装叠好装箱。
一般演《红灯记》全场的时候不会出什么问题,就怕演选场,搞不好就忘了带什么东西。有一次去一个农队慰问演出,那天以小节目为主,《红灯记》只演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在那一场戏里,李玉和进家门后铁梅要帮他把大衣脱了。结果我忘了带李玉和的大衣了。快演到这个节目时我才发现。没辙了,我只能去跟指导员(李玉和)实话实说。我想,我主动承认错误并且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领导就会原谅我。所以我跟指导员说:“您假装做个脱大衣的动作,估计观众也看不出来”。这句话可把指导员气坏了!他特别严肃地对我说,“这事儿能假装吗?”现在想起来我都为那时自己耍小聪明而脸红!

这位大家已经认识了,她就是和我同一天加入宣传队、经常和我一起当“镇台之宝”、聊天聊到忘了上场的荣力军。她舞姿优美,身材纤细,令人羡慕地吃啥都不长肉,是宣传队舞蹈节目的主力。《红灯记》里她也演女游击队员。

这是宣传队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农兵学演革命样板戏”汇演大会上的演出剧照。照片里面没有我,因为那时我还不是宣传队员。把这张照片放在这儿,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剧终时的亮相动作。说来也是遗憾,那时胶卷太珍贵了,我们这些群众演员很少留下剧照。
第七次集中时,为了充实舞蹈节目,队领导决定复排芭蕾舞剧《白毛女》第一场。我们排练的《白毛女》第一场是上海芭蕾舞学校较早的一个版本,由蔡国英、顾峡美、凌桂明担任主演,曾拍成过黑白电影。这个版本和1972年由茅惠芳、石钟琴、凌桂明主演的彩芭蕾舞《白毛女》有些细节不太一样。比如,黑白版本中大春和喜儿的恋人关系还是比较明确的,剧中也有一些两个人相亲相爱的动作。而1972年的彩色版中大春和喜儿的关系设定很模糊,让人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恋人关系还是乡亲、邻居的关系。
估计现在知道老版本的人不太多。我们业务学习时曾有几次组织观看这部黑白影片。这次复排主要角色还是由原来的老队员担任,喜儿由严琳扮演,大春由朱彦南扮演,黄世仁由胡明山扮演,穆仁智由张维善扮演,他们轻车熟路,排练起来很顺利。每次排练看他们跳,我都特别享受。
但群众角色都换成新队员了,比如跳《窗花舞》的四个女孩儿换成了荣力军、禄广芬、施燕芝和我,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天大的考验!我们虽然都有一些舞蹈基础,宣传队集中时也都参加练功,但毕竟是业余宣传队,每次回到原单位工作几个月,功又都回去了。再说,我们从未穿过芭蕾舞鞋,更没有立过脚尖。而我们这几个人里面年龄最大的已经19岁了,最小的也16岁,这个年龄才开始压脚背、立脚尖,甚至还要立着脚尖做一些技巧动作,这其中的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结果没练多久,小荣的脚就出了问题,几乎不能走路了。到医院拍片检查才发现她脚上比别人多长了一块副舟骨,医生说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崴脚,不能跳芭蕾舞了。怎么办?只好临时换人了!领导决定让陈毓芬来跳小荣的位置,由我来负责教陈毓芬这段舞蹈动作。为了跟上大家的进度,陈毓芬也真是很拼,不叫苦不怕累不喊疼。大概是练得太苦了吧,没过几天她就病了,高烧39度多不退。距离领导审查节目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心里很是着急。
为了排练这个节目,我们吃了多少苦,忍了多少痛!我们每个人的脚都一次又一次地磨破了皮,脚趾头连同脚趾甲都是黑紫的,伤痕累累。每次练习我们都是忍着痛咬牙跳。这个节目要是流产了,我们这些苦不都白吃了吗?不行,我非得教会陈毓芬不可!有一天晚上,陈毓芬发着高烧都睡下了,又被我拉起来到院子里练《窗花舞》。后来领导知道了这件事,很婉转地把我批评教育了一顿。因为时间太仓促,排练过程中又有些伤病情况,这个节目最终还是没能通过审查,只是给干校领导汇报演出过一次。但这次复排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甚至到现在我还记得“窗花舞”的动作。

宣传队第七次集中的主要成绩之一就是大幅度、全方位地改编了当时在观众中已经很有口碑和影响力的小歌剧《红军帽》。整个剧本几乎是重写了一遍,删掉了一些可有可无的情节和人物,进一步突出了作品主线,使故事情节更加合理、紧凑,剧情更加引人入胜,主要角色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唱段及音乐伴奏更加专业。音乐方面更是进行了全面的提升。原来的乐队是当时业余宣传队普遍的“标配”:民乐为主+手风琴+大提琴。新版本增加了一段“序曲”合唱,无论是作曲还是伴奏(加上了管弦乐)都非常有气势。
可以说每次演出只要音乐和序曲合唱一起,专业范儿立马爆棚。由于剧本、剧情的改动,每个角色的唱段也基本都是重新填词作曲的。新的唱段无论是歌词还是音乐都非常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旋律优美,还揉进了宁夏花儿的元素,从而使得这部小歌剧有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新版本《红军帽》由胡文伟饰演老红军,丛利饰演奶奶,张桂香饰演军医,严琳饰演奶奶的孙女继军。


说起来我跟《红军帽》很有渊源。无论是老版本的《红军帽》还是新版本的《红军帽》,我都演过,当然都是作为替演上场的。实话说,当时能参演这部“重头戏”我真的感到特别光荣,也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演好。在老版本《红军帽》里,我扮演老红军常播的女儿常新征。剧中没有我的唱段,只有一些台词。1971年7月16日,我们去校七队巡回演出。当时我父亲在校七队下放,那天他也坐在台下看我们演出。巧的是扮演老红军的张乃栋就是校七队的,观众都认识他。当我在台上喊张乃栋“爸爸”时,台下一片哄笑,有人还喊“叫错了”,“他不是你爸爸!”
在新版本《红军帽》里,常新征这个人物去掉了,新增添了一个女孩子的角色,叫继军,是老奶奶的孙女。我替演的就是继军。继军有两段独唱,都很好听,我到现在每一句歌词还都记得。可惜我嗓子条件不好,再加上每天演出都是连唱带跳的,声带疲劳总是恢复不了,有时上台时根本唱不出声音来。于是,说来惭愧,我就想到了假唱。我请孔祥瑜在后台用麦克风唱,我在台上对口型。每次演出完毕不少观众都夸赞我唱得好,嗓子好。为了集体的荣誉,我也只能咬牙默认是我唱的了。
为什么观众说我唱得好?因为孔祥瑜是我们宣传队的担纲女声独唱和金牌报幕啊!她的歌喉清婉,音色纯净,高音穿透力很强。她演唱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曾经在宁夏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放。她还为电影《五七指示放光芒》演唱了主题歌。这首歌的作曲是著名作曲家潘振声(1933~2009)老师的代表作。潘振声老师曾创作过《一分钱》《小鸭子》《好妈妈》《嘀哩嘀哩》等。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资料现在都找不到了。

这位就是孔祥瑜。她的年龄在宣传队里属于比较小的,大家都叫她“小瑜子”。但她可是队里的“小大人儿”,管理着队里的急救药箱。谁要是临时有个头疼脑热小伤小病的,都去找她处理。此外她还管着队里的化妆用品。一般我们演出化妆的底色都是她负责调。那时演出都是用油彩化妆,卸妆时小瑜子会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浸满了豆油的棉球。我们要先用豆油把脸上的油彩擦下来,再去洗脸,否则脸根本洗不干净。
那时不知是因为小瑜子她年龄小身体不好,还是因为贺兰山的气候太干燥了,她经常流鼻血,而且一流起来就很难止住。大家最怕她演出的时候流鼻血了,可怕什么来什么,有好几次演出前她鼻血流得怎么也止不住,无论用冷水敷,还是用棉花堵,都不起作用,把她急的直哭,也让大家心疼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下只好让别人替她报幕,再把她的独唱往后一推再推,直到她能上台为止。有时候流血不是特别厉害,她就用棉花堵着鼻孔上台演出,一个节目下来,血把棉花都浸透了。小小年纪,这么有担当,怎能不令人感动!
干校下属军马场有一个女子放马班,是干校的先进集体。根据她们的事迹王念五指导员为首的创作班子创作了歌曲《红色女牧工》。为了更好地表现女子放马班在贺兰山的高山峡谷、在西大滩的戈壁草原纵马奔驰的英姿,我们又将这首歌曲改编成舞蹈。后来队里又请来了自治区著名的舞蹈编导王蓓老师。王蓓老师对这个舞蹈再次进行了深度加工,在舞蹈中加进了一些独舞和双人舞的片段,舞蹈中间又加了一段音乐,使这个舞蹈故事性更强,内容更加充实。


这是《红色女牧工》的演出剧照。左起孔祥瑜、张亚文、陈毓芬、何平、徐玲、张桂香、严琳、荣力军
1970年8月贺兰山暴发了一次特大山洪。为了尽可能保护干校周边公社老乡的房屋财产和地里的庄稼不受损失、少受损失,干校子弟兵做出了巨大牺牲,把洪水引到了自己这一边,因此干校大面积受淹。配乐诗表演《抗洪凯歌》就是根据这件真事所创作的。诗作者是张政诚,大家都叫他“张胖”,好像是校部的秘书。我还记得他写好诗后在宣传队的临建活动房给我们朗诵的情景。他站在小小的窗户前,借着窗口透进来的光亮,朗诵得激情澎湃。“八月的贺兰山,天空显得格外的晴朗。金色的稻田,火红的高粱,满树的苹果压弯了枝,今年丰收在望……”
1971年7月21日至26日,宣传队奉命到石嘴山市石炭井矿务局及下属各煤矿进行巡回慰问演出。干校男女篮球队也同时到石炭井矿务局进行篮球友谊比赛。
这次我们也是带去了两台节目,一台是京剧《红灯记》全场,一台是小节目。到达石炭井矿务局的第一场演出是在矿务局剧场。这个剧场在当时来说,舞台设施、音响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队领导决定那天晚上先演出京剧《红灯记》。下午三四点钟,装台、布置灯光的队员就提前赶到了剧场。小朱(朱彦南)虽然是宣传队舞蹈类节目的男一号(现在叫“首席”),但在京剧《红灯记》中的戏份并不重,只扮演和鬼子打斗的八路军战士,因此他还负责演出的灯光效果。
据小朱自己回忆,石炭井矿务局剧场的舞台很不错,台角还有灯光控制观查口。不足的是灯光色彩比较单一,缺乏变化,所以他就拿来“彩色灯光景片”插到聚光灯前,初试效果不错,于是他就上到礼堂顶棚的天桥上按剧情把所有的灯都插上不同颜色的景片。就在即将全部做完时,大概是剧场工作人员试电吧,一下子把台前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开了。因为小朱一直在礼堂顶棚的黑暗处作业,当所有的聚光灯都打开直射到他脸上的时候,就造成他短暂的强光性失明。一时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一脚踏空,人整个就从几层楼高的天花板上摔了下来,重重地砸在了观众席前排的横条椅上。因冲击力很大,造成左肩胛骨骨折,左肺破裂,开放性血气胸,骶骨压缩性骨折。
小朱受伤的时候我们正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准备化妆,突然队领导通知我们集合开会。当时我以为队领导要进行演出前动员呢,可当我走进会议室,立马就感觉气氛不对。领导们一个个神色都特别凝重。人到齐了之后,沈启新副指导员开始讲话。但话还没出口,他的眼圈就红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小朱受伤的过程和受伤的严重程度。
沈副指导员告诉大家,小朱被送到矿区医院后曾短暂地苏醒了几分钟。他还惦记着会不会影响当晚的演出、他的角色由谁来替演。说到这里,沈副指导员声音哽咽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们大家听到这里也是既震惊又揪心,特别担心小朱的安危,很多人都哭了。大家纷纷表示要到医院给小朱献血。沈副指导员告诉大家,手术的血液供应没有问题,很多矿工兄弟都等在手术室外准备给小朱献血。矿务局也已经派专车去银川接专家前来给小朱手术、会诊,另外也已经通知了小朱的父母,他们也会很快赶来。队领导向全体队员发出号召,向朱彦南同志学习,以更加高昂的精神面貌和更高的质量完成当晚的演出任务,以实际行动报答矿工兄弟们的深情厚谊。
由于小朱受伤,他扮演的八路军战士的角色临时交给胡明山扮演。这是一段武打戏,明山之前从没练过。扮演鬼子兵与他对打的是李兴福。他俩接到任务后饭都顾不上吃就开始练,一直练到演出开始。但毕竟他们俩人配合的太少,在演出中明山还是不小心一刀劈在了李兴福的头上,把李兴福的头皮劈了一个大口子,鲜血顿时就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把他戴的鬼子兵的呢子帽都浸透了,血顺着脖子流到了衣领里。但李兴福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一直坚持完成了整场演出。直到得知他要去医院缝合,我们才发现他受伤了。给他缝合头皮的医护人员都难以相信他带着这么大的伤口完成了演出,都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那天晚上的演出非常成功,矿工兄弟们的反响极为热烈。我们在石炭井共巡回演出了6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受到矿区领导、矿工兄弟和家属的热烈欢迎。有时候我们要一天演出两场。每次演出都是剧场爆满,有不少观众没有座位就站着看我们的表演,那真是台上台下水融。
经过医学专家的会诊手术,小朱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而这时,他的父母也赶到了石炭井。为了向矿务局领导、医学专家、矿务局医院医务人员和为朱彦南献血的矿工兄弟们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也向朱彦南的父母表示慰问,我们在矿务局招待所会议室里专门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小型演出。
那天演出的节目不多,主打节目是新版《红军帽》。扮演老红军、奶奶和军医的都是原班人马:胡文伟、丛利、张桂香。由于原来演孙女继军的演员严琳这次没来参加巡回演出,领导决定让我临时替演继军。在那之前,我也就临时替演过两三次吧,而且一直也没怎么好好排练过,只是自己看的次数太多了,觉得都记下来了,其实心里还是没底,每次都是硬着头皮上台,侥幸过关。
但这次情况不同。从我们到达石炭井矿务局那天起,就时时处处感受到矿务局领导和矿工兄弟们对我们的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就连我们走在路上、在食堂就餐、或者在礼堂跟他们一起看电影《南江村的妇女》,他们都对我们报以友好的微笑和热情的掌声。这次小朱受伤后,矿务局领导全力配合,矿务局医院奋力抢救,矿工兄弟们更是争先恐后为小朱鲜血,这些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鱼水情。我暗下决心,一定好好演,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台下的观众。所以一直到上台前,我还都在默默背台词。
节目开始后,一切顺利。胡文伟、丛利、张桂香他们情绪进入很快。演到动人之处,他们都是声泪俱下,台下的观众也无不深受感动,都不时地擦眼泪。而我大概是太想演好、太紧张了,一直在心里默词,根本进不了戏。看到他们几个在台上或者热泪盈眶或者泪流满面,台下的观众也都哭的稀里哗啦的,我硬生生的是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最要命的是,就在老红军和奶奶回忆当年即将相认、剧情马上要达到高潮时,我忘词了!轮到我说了,可是我头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接什么好!他们几个人也发现不对,都转过脸来看着我。现在回头想这件事,当时我完全可以随便说一句话蒙混过去,比如:“那后来呢?”
可是我居然又自作聪明了,对老红军说:“莫非您就是当年住在我家的红军战士?”天哪!奶奶和老红军还没相认,他们的高潮唱段还没开始,我就提前剧透了!当时他们那几位都是一脸的惊愕和尴尬。不过幸亏他们表演经验丰富,也就是停了一瞬,就把戏接了下去。可是我知道,我冒那一下子,把他们的眼泪都吓回去了!唉,好好的一个节目,又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结果都被我给搞砸了。那天领导没有批评我,可是我自己连死的心都有了!
宣传队的第七次集中从1971年6月9日开始到8月10日结束。集中结束后,有15名队员没有像往常那样返回原单位,而是被留了下来。一部分年轻队员被送到银川歌舞团学习乐器,而由几位队领导牵头的部分创编人员则又开始策划新节目。我们接到任务,9月中旬将代表总后企业局前往位于湖南湖北交界处的总后2348工程进行慰问演出。
我是被派到银川歌舞团学习乐器的队员之一。领导让我学习打扬琴。同去的还有张玉鹏、孔祥瑜、朱彦南(小提琴)、张桂香(二胡)、赵晓红(琵琶)、严琳(大提琴)、林萌(手风琴)、胡明山(中阮)等。我们这些人里有的原来就是演奏这些乐器的,他们属于进修提高。而我则纯属是白丁一个,过去从来没打过扬琴。领导这样安排,一是因为赴湖南湖北演出有人数限制,二是领导也有意给宣传队“消肿”,把宣传队打造成一支人员精良,一专多能的队伍,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队员都会演奏乐器。
银川歌舞团负责教我扬琴的老师姓张,他人特别好,毫不嫌弃我是零基础,对我极为耐心,从怎样握琴竹,到轮竹、颤竹这些基本技法一点一点地给我讲解。针对我们演出任务急迫,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练习基本功上,他专门为我制定了一套非常实用的练习方法:即照葫芦画瓢。他选择了一些简单的乐曲,一句一句地给我示范他是如何演奏的,让我模仿他的方法练习。这样,很快我就能奏上几首曲子了。
有了初步的成就感,我练习的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主动把宣传队的一些保留曲目拿来练习——其实纯属乱弹琴,没有丝毫的章法。张老师也不怪我,心平气和地给我纠正。慢慢地,我有了一些进步,起码偶尔在乐队里滥竽充数一下,观众也看不出来。我们宣传队主要打扬琴的是胡旬老师。只有在他上场演其他节目时才由我去打扬琴。所以我需要练会的曲子也不是很多,慢慢地我也都能应付下来了。这次短短几周的进修对我们意义非凡,虽然是突击训练,但是有专业老师每天一对一全天候的陪同指导,我们都有了很大提高,宣传队的整体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1971年9月2日,宣传队第八次集中。短短的9天之后,即9月11日,我们就在干校子弟中学(现银川第八中学)礼堂演出了一场小节目。这么快就能拿出节目来,主要是因为第七次集中后宣传队其实并没有完全解散。8月初长春兽医大学宣传队来干校访问演出,宣传队又临时召集起来,与兽医大学宣传队切磋交流,并于8月17日在银川红旗剧场为庆祝自治区党代会的召开合演了一台节目。两支宣传队各自拿出自己的“看家”节目,又在一起赶排了几个合演节目。这场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台下观众反响十分热烈。
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在跳“开场歌舞”时,有两个集体造型。我和另外一名女队员被安排在两侧台前的位置下竖叉。结果那天我穿的解放鞋号有点儿大,鞋带也没系得很紧,站起来的时候就把右脚上的鞋蹭掉了。见此情况,忘了是潘春还是谁一脚就把我的鞋踢到边幕里了。可是节目还没完,我还得接着跳啊,只好光着一只脚把这个节目演完了。有了这段时间的合作演出和交流,有很多节目都基本成型了。所以第八次集中没有几天,我们就开始新一轮的演出了。
当然,新节目的排练始终没有中断。第八次集中的主要任务就是排练去“两湖”慰问演出的节目。9月18日,我们在干校校部食堂把要去“两湖”演出的节目预演了一遍,得到了干校领导的肯定和观众的好评。9月21日我们踏上了慰问演出的征程。
这次赴“两湖”执行慰问演出任务的是一支非常精干的小分队,总共不到30人。所有的服装、道具、乐器以及个人用品我们都是随身携带,所以我们在火车站等车、换车的时候非常引人注目,经常引起群众的围观。那时火车车速很慢,从银川到长沙要两天多的时间。我们在火车上积极做好人好事,把车厢列车员送水、扫地、拖地的活儿全包了下来。同时也应列车长的邀请在各个车厢为旅客表演小节目,受到了列车乘务人员和观众的交口称赞。
总后2348工程是我军大型石化“合成纤维”基地,其历史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日,中央发出“绝密”中发(65)45号《关于批准建设大同、岳阳两个炼油厂的通知》:“同意建设山西大同、湖南岳阳两个炼油厂,建设规模均定为每年加工原油150万吨。”根据国家“山、散、洞”的战略布局,石油工业部选址在湖南省临湘县陆城、路口人民公社的长岭地区,兴建150万吨/年,时为我国第三套大型炼油厂——岳阳炼油厂。后来,为了统一提升65式军装的面料、增强其耐用性,减轻战士负重,总后领导决定利用炼油厂“废气”生产“化学合成纤维”。1969年9月7日,经周总理批准,“中国人民总后勤部第2348工程指挥部”诞生了。

同年6月,总后研究决定,将化工生产管理局所属工厂(企业)直接编入军需企业序列,依次给2348的工厂实体授予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3101至3110(工厂)军队序列番号,即:3101厂—(长岭)炼油、3102厂—锦纶、3103厂—涤纶、3104厂—腈纶、3105厂—橡胶、3106厂—环氧树脂、3107厂—供排水、3108厂—热电、3109厂—机械、3110厂—(蒲圻)纺织。3110厂下辖3552厂、3553厂、3554厂、3616厂。基建高峰时期,参建人员在相距百里的湖南岳阳市云溪、湖南岳阳临湘、湖北蒲圻市(1998年更名为赤壁市)的三个工地上有近10万之众。
在包括路程在内的22天时间里,我们在湖南云溪总后企业部化工局、2348工程3101、3104、3106、3110、长岭炼油厂、陆城管理局等单位共演出了18场。我们的这台节目经过精挑细选,质量较高,形式新颖,都是宣传队具有代表性的节目。有小歌剧《红军帽》,小歌剧《抢筐》、男声四重唱《六盘山》,舞蹈《红色女牧工》、女声表演唱《六二六指示放光芒》、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等。
为了歌颂积极投身三线建设的劳动者,我们专门排练了小歌剧《抢筐》,由胡文伟、严琳、朱彦南表演。这个小歌剧实际上是一个喜剧小品,无论是语言还是这三位战友的表演都非常贴近生活,每次演出观众中都是笑声不断。最后压轴的节目是器乐合奏《地道战组曲》。这个节目我们全体队员近30个人都上场演出,人手一件乐器。每次大幕一拉开,光这阵势能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了。“哎,拉大提琴的不就是演《抢筐》里卫红的那个人吗?”“拉小提琴的那个女孩儿不就是刚才唱独唱的吗?”而此时我心中的自豪感就油然而生了——甚至忘了自己基本是个滥竽充数的,除了《地道战组曲》,会打的曲子并不多。
当时有这样一句话,扬琴是民乐队的指挥。每次我都在前排C位正襟危坐,先假事儿事儿地环顾一下左右,看大家都准备好了,再像乐队指挥那样用力地抬一下双臂,在我的琴竹打在扬琴弦上的同时,乐队开始演奏。《地道战组曲》的音乐并不复杂,基本是根据电影《地道战》贯穿始终的主题音乐改编的。当时没什么电影看,《地道战》是每个人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影片了,对电影里的音乐人们也都是耳熟能详。什么时候鬼子进村了,什么时候老钟叔跑着去敲钟,什么时候“不见鬼子不挂弦”大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能与我们产生很好的共鸣。
说我是滥竽充数吧,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在这个合奏里,樊靖华队长给我安排了一个乐句的独奏。为了这一句,我真是呕心沥血勤学苦练啊,可以说是练了成千上万次。合奏时扬琴声音小,就是打错一两个音,观众也听不出来。可是这句独奏事关重大,要表现出发现鬼子进村了,老钟叔冒着生命危险赶去敲钟的紧迫感。可是越想敲好就越敲不好,平时练习的时候,这一句敲得特别准,可一到演出的时候,大概十次有五次我都会把一个音敲到琴码子上,发出刺耳的敲木头的声音。每次打错了,我满满的自豪感瞬间就变成无地自容的愧疚了,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次在“两湖”的巡回演出我特别开心快乐,我们还见到了很多从咱们干校去的知青。他们很多都是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战友。见到我们他们都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演出后他们很多人都来到后台看望我们。当时正值中秋节前后,我的发小,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马爱玲还为我买了很多月饼,让我特别感动。
演出之余,我们还与2348工程下属的一支宣传队进行了学习交流。他们对我们的节目是由衷的喜欢,说我们的男声四重唱《六盘山》唱得像广播里的一样好听,说《红军帽》里的老红军胡文伟一出场就让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有几个女孩子教给了我们一个以纺织女工为题材的舞蹈《根根银丝连北京》,我们也把《红色女牧工》教给了她们。
这次巡回演出还有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经历:队领导组织我们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游览了毛主席青年时期在长沙活动的纪念地橘子洲头和清水塘,我们还乘竹排游览了湘江,亲身体验了“湘江水向北流”。
从韶山回到长沙后,我们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队里专门举行了赛诗会。每个队员都朗读了自己写的诗,抒发参观毛主席故居和革命纪念地的感想。
我们在贺兰山西大摊上呆了几年,把城市是什么样都忘记了。到了长沙后觉得长沙特别繁华,很想转转看看,但队里规定不能私自外出。记得有一天晚饭后,赵晓红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就跟着她前后脚出去了。没走多远我们就看到一个拉车卖香蕉的。香蕉啊!那几年我们都忘了香蕉是什么味儿了!赵晓红立马掏钱买了五毛钱的,忘了多少斤了。反正我俩拼命吃,想在回招待所之前吃完,不能让领导发现我俩私自外出了。后来我俩撑得都快吐了,香蕉还是没吃完。赵晓红说,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

赵晓红是宣传队乐队的弹拨乐全能演奏员(月琴、琵琶、中阮、扬琴等)。由于有一副好嗓子,她也是女声小合唱、京剧清唱这类节目的主力。此外,赵晓红还是宣传队创作组成员之一。那时我们去一些单位演出,常常要收集这个单位的情况和先进模范人物事迹,然后由沈启新副指导员、张振华副队长、赵晓红和我连夜编出一个小节目(多数是群口快板的形式),第二天就上台演出。那个年代有很多现成套路的句子,再加上老沈、老张他们文化水平高,节目编起来多数情况下还算顺利。
但也有大家都被卡住了、都困得睁不开眼了,还是怎么也编不下去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好把编完的词先背下来再说,反正第二天要演。就这样背着背着,卡壳的地方突然又来了灵感,又能继续往下编了。因为有很好的时效性,说的又都是这些单位观众熟知的人和事,这样的节目一般都比较受欢迎。

这里还要介绍一下宣传队男队员里年龄最小的林萌。我们去“两湖”演出时他刚刚16岁。他是宣传队的手风琴演奏员。在当时的业余宣传队里,手风琴可以说是乐队中最重要的乐器了。可是我们到达2348工程指挥部没多久,就发现林萌不对了。他突然发高烧不退,脸肿得像个包子,眼睛肿得眯成了一条缝。经医院检查,他得了急性肾炎。要按现在,他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卧床休息。可是他要是住了院,手风琴谁来拉?演出怎么办?而且,当时舞台音响效果普遍都很差,乐队全靠手风琴保证音量呢。要是没了手风琴这乐队成了什么了!林萌深知领导的难处,主动提出白天去医院打针输液治疗,晚上照常参加演出。他小小年纪为了演出能这样于自己而不顾,让我们特别受教育。我们慰问演出结束刚回到干校他就被收住院了。
其实林萌非常聪明,也是多才多艺。他除了演奏手风琴外,还会作词作曲。他在野营拉练途中创作过的一首歌,旋律激昂,也很好听:“戈壁滩上披银装,贺兰千里摆战场,数九寒天来拉练,风尘滚滚行军忙!”他的保留节目是手风琴独奏《牧民歌唱毛主席》。我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到干校各队、点进行慰问演出的时候,他这个节目是必上的。
10月13日我们在2348工程3110厂礼堂进行了最后一场演出。两天后,队领导突然宣布上级紧急指示,让我们中断一切演出返回干校。隐约中我们都觉得出了什么事,但又猜不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又不能问。我们是10月17号返回银川的。10月19号宣传队第八次集中宣布结束。我们再次回到了各自的原单位。后来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发生了“9.13事件”。
1972年2月1日,宣传队第九次集中。第九次集中时宣传队人员又进行了一些微调,韦荔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段加入宣传队的。

这位就是韦荔。她形象出众,嗓子甜美,能歌善舞。我们参军后不久她就被借调到军事博物馆当解说员去了。在宣传队里韦荔主要担任小合唱、表演唱和舞蹈表演。

经过短短10天的排练我们就开始演出了。这次排练的节目基本以我们赴湖南湖北慰问演出的节目为主,因为这台节目大多数没在干校演出过,包括我们从2348工程指挥部宣传队学回来的舞蹈《根根银丝连北京》。当时电影《龙江颂》刚刚在全国上映,我们乐队的鼓师闫老师感觉《龙江颂》的唱段非常好听,就用我们那台笨重的老式录音机从广播里把《龙江颂》的一些唱段录了下来。他从中选了一首《手捧宝书满心暖》,一句句地把所有的伴奏音乐和配器扒了下来,改编成一首女声京剧联唱,由张桂香领唱,丛利、赵晓红、孔祥瑜、韦荔、陈毓芬、荣力军和我都参加了合唱。《龙江颂》的唱段当时在银川还没有人表演过,我们属于抢占先机,每次演出都令观众感到很新奇,反响非常好。
从2月11日到3月17日,我们共演出了27场,全干校所有的学员队、农队、马队我们都跑遍了,此外还到银川机砖厂、银川通用机械厂、银川橡胶厂、银川长城铸造厂、芦花台公社进行了慰问演出。
3月17日我们结束了最后一场演出。但宣传队并没有解散,全体队员都留了下来继续创编新节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一位年轻队员在执行一次外出采访任务时被一辆拖拉机撞伤,造成颅底骨折,不幸牺牲了。
因公牺牲的年轻队员叫张家明。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8年了。他牺牲的时候才刚满18岁。在宣传队里,我们都管他叫向阳子,这既是因为他上妆之后,颇有些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的李向阳,眉宇间英气十足,同时也因为他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特别温暖、善解人意、充满正能量的阳光男孩。向阳子1954年出生,在男队员里除了林萌就是他最小了。可是他特别懂事儿,他的沉稳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远远超出了他的年纪。
日常训练中,他谦虚好学,一丝不苟,细心琢磨每一个动作,进步特别快;出公差勤务时,他积极主动,不怕吃苦,认真负责,是队里干体力活儿的绝对主力;在评定“五好战士”等荣誉、机会面前,向阳子总是先人后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在湖南湖北巡回演出时,无论到达哪个地方,自由活动的时候总要留下人看管全队的服装、道具、乐器等物品。而每次都是向阳子主动要求留下来为大家服务。
那时我对向阳子总是抱着一种既感谢又愧疚的心情,因为每一次布置任务时,我都在心里暗暗希望领导千万别让我留下来看东西。在那个年代,能有机会到这些没去过的地方看看转转、参观游览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能够说是天大的幸运啊!我想,十几岁的他心里一定也特想和大家在一起玩儿吧!但向阳子就是这样,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他能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需求和快乐,最后把自己宝贵的生命也留在了广袤的西大摊上,让青春年华永远定格在了18岁。
得知他牺牲的消息之后,宣传队所有的队员都极为悲痛,很多人都失声痛哭。我们几个门诊部出来的宣传队员赶回门诊部亲手帮他擦拭了脸上、身上的血迹,连夜为他清洗了血衣。在他的追悼会上,他姐姐朗诵了他笔记本上的一首诗《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诗中写到:“每当我看到冉冉升起的朝阳,总在想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是个什么样?每当我戴上金灿灿的像章,总感到毛主席就在我的身旁……”
这是宣传队第九次集中时的合影。可惜的是我们的身边再也没张家明帅气的身影了!
1972年4月5日,宣传队第九次集中结束。随着干校的撤销,宣传队员们也都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自此,宁夏银川总后五七干部劳动学校思想宣传队成为了历史。但这段历史永远深深地留在了所有宣传队员的记忆中。
卞化清,曹红兵,陈桂英,陈家林,陈树亭,陈新华,陈毓芬,程庭国,丛利,杜文生,樊爱萍,樊靖华,何平,侯建新,胡明山,胡文伟,胡旬,黄宝,居月昆,贾小平,康(),孔祥瑜,李红武,李兴福,李芷汀,李祖荫,林崇浦,林萌,刘军,刘泉,刘同,刘岩松,刘耀清,刘玉昆,逯广芬,吕森林,潘春,朴相浩,齐毓怡,荣力军,沈启新,施燕芝,史丽娜,仝瑞亭,王德祥,王桂珍,王金章,王念五,王淑环,王顺德,王援生,王召,王治政,韦荔,吴成鸾,徐玲,薛玲,闫瑞西,严琳,易时玉,郁正钧,张桂香,张宏友,张家明,张乃栋,张蓉蓉,张维善,张秀慧,张亚文,张艳,张玉梅,张玉鹏,张振华,赵军武,赵晓红,周新华,朱彦南

上面这张图片是我参军入伍登记表的一部分。1970年12月9日银川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我参军入伍。今年12月9日是我们总后贺兰山五七干校的知青集体入伍50周年,也是我加入干校宣传队50周年。我想用这个美篇对那段历史做个回顾,这也是我向参军入伍50周年纪念日献上的一份心意。
把宣传队的故事写下来,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徘徊了好几年。但由于很多战友联系不上,一直不知道怎么来下笔。现在完成的内容也仅是根据我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编写的。由于年代久远,自己了解的情况有限,再加上记忆力减退,这个美篇中有很多该写却没有写到的地方,也肯定有一些记忆上的失误,希望战友们予以谅解并加以指正。更希望战友们积极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我们大家一起不断充实、完善这个美篇。在此,我也向所有提供资料、图片的战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的无私帮助,这个美篇也不可能与大家见面。战友们提供的离开贺兰山之后的照片、资料我将编辑在《贺兰往事之干校有个宣传队》(下)中。

作者徐玲女,1969年10月参加工作,1970年12月入伍。1975年被选送到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学习。毕业后在军械工程学院任教,副教授、技术五级。2013年10月退休。